|
白癜风是否传染 第72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值此迷影狂欢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了14年的一部以色列电影,名字为《教师》(הגננת),执导本作的是往届柏林金熊奖得主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 电影的情节本身很好理解。女主妮拉是某个以色列幼儿园的幼师,她嗜诗如命。一天她注意到幼儿园里名叫波兰克的五岁男孩有诗人的天资,他经常会突然说“我有一首诗”而后开始一句一句地念出。在妮拉眼里那都是极好的诗,她甚至记录下来拿到诗歌爱好者沙龙去朗诵,在她看来,世界是黑暗,抹杀诗人的,诗人就是要“对抗世界的本性”。可后来,两件事的出现使得全片诗意和谐的氛围急转直下。首先是妮拉带着男孩去参加诗歌朗诵大赛却遭到全场观众的嘲讽,其次是妮拉和男孩之间奇妙的关系被男孩从商的父亲得知,父亲将男孩带离幼儿园并威胁老师要报警。妮拉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即她“绑架”了小男孩,因为她要带着诗人远离这个世界。接下来是本片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剧情,小男孩趁妮拉洗澡时,将妮拉反锁到厕所,用妮拉的手机报了警。全剧终。 在谈论“诗人”这个点之前,我想把韩国导演李沧东于2010年执导的电影《诗》拿过来比较一下。《诗》的主角是一个跟本作女主一样爱诗如命的老太太,哪怕电影里她的孙儿和别的问题孩童共同强奸一个女孩至死,她都似乎一致沉溺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中。但与《教师》的女主一样,她参加沙龙,他参加诗歌创作班,这些都没有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或者说,在行为层面上创作出一首特别好的诗。最后,她终于开始正视了女孩经历的事情,她拜访了女孩的母亲,走过来女孩被强奸前的土地,并在最后叫警察带走了自己的孙儿。李沧东动人的镜头将老太太的背影化为了女孩的回眸(蒙太奇)。老太太的行为在最后一刻使得她在影像层面成为了饱满而神秘的电影人物,虽然可能与“诗人”完全不搭边,其行为更像是良心发现之人。 这点与《教师》是不同的。《教师》的最后,妮拉在厕所里指导男孩报警。在某种意义上,她找到了一条叫男孩逃离这个污浊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出名”。电影的结尾的镜头,是男孩的面部特写。 我们不难意识到,本次绑架事件会让男孩和他的诗公之于众,或许会令他成为以色列公认的新一代诗歌天才?谁知道呢。但这个行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种“技巧性”的美感。好比一个犯人的完美犯罪,将犯罪做到极致的人,就不仅仅是“罪犯”,他会被私人侦探和同行评价为“艺术家”;将美食做到极致的人,就不仅仅是“厨子”,他会被顾客和美食界尊为“艺术家”;将对诗人的崇拜做到极致的人,就不仅仅是“爱诗之人”,她会被观众和后世尊为什么呢?妮娅的终局和小男孩的作诗机制有着相同的神秘感,但与《诗》中老太太的良心驱动似乎不同,这份神秘感和“行为艺术”驱使妮娅抵达了“诗”的本性。 以上是我对电影和电影作者的分析。然而,作为一个教育新闻从业者,我还想谈一个很小的点,虽然很小,但越思考越发觉有拿出来讨论的价值。那就是,诗人能不能被教育出来? 20世纪非常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曾经在他的文章《诗人何为》这样写,【在贫困时代时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说神圣】。由此申发出一个论点,诗人是向世界之外探索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日益为语言所建构和禁锢时,诗歌就是站立在语言之外的存在。这绕口的说辞再简单一点便是,写文字就好比下棋,大多数人都想把棋下的漂亮,可诗人却只想把棋子下到棋盘外。 片中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和镜头,妮拉为了弄明白这个五岁的孩子到底是如何作诗的,他让孩子和她一起蹲下,还补充这是小猫咪的视角。 这里意味很显然,老师在观察这个孩子是如何观察这个世界的,可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诗歌一定需要产生于对世界的观察吗?二、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孩子的视角?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或许能说明诗人能否被教育出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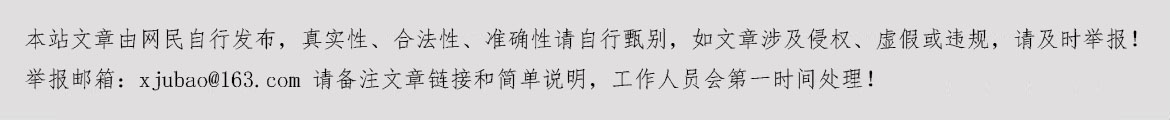
|